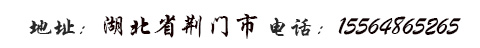张锦池先生丨天下治乱,系于用人论西游记
|
湖南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http://m.39.net/pf/a_5789682.html 一、明清以来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红楼梦》的命意问题,是个聚讼不休的问题。《西游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妨让我们具体看看明清以来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明人袁于令《西游记题词》,道是:“说者以为寓五行生克之理,玄门修炼之道。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而必问玄机于玉匮,探禅蕴于龙藏,乃始有得于心也哉?”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则云:“《西游》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亦推测说:“《西游》、《西洋》,逞臆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 清人尤侗《西游真诠序》认为:“《西游记》者,殆《华严》之外篇也。……盖天下无治妖之法,惟有治心之法,心治则妖治。记西游者,传《华严》之心法也。”可刘廷玑《在园杂志》却认为:“《西游》为证道之书。……借说金丹奥旨,以心猿意马为根本,而五众以配五行,平空结构,是一蜃楼海市耳。”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则从而反驳说:“今《西游记》,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明显易见,确然可据,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耳。亦何有于仙佛之事哉?”张含章《西游正旨后跋》遂调和之,倡言:《西游》之大义,乃明示三教一源。故以《周易》作骨,以金丹作脉络,以瑜伽之教作无为妙相。”一语惊四座的还数黄人,其《小说小话》云:“房中术差近。”理由是:“请问金箍棒为何物?” 要之,明清两代诸家,皆各执一说,或看作求放心之喻,或看作瑜伽心法,或看作金丹采炼,或看作《大学》诠释,或以为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真是标奇立异,五花八门,仿佛妖怪肚子里都满藏三教哲理。 一反此等成说的是胡适,其《〈西游记〉考证》云:“《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1]鲁迅则一则汲取了胡适的看法,一则又汲取了谢肇淛的看法,其《中国小说史略》云:“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假欲勉求大旨,……盖亦求放心之喻。”[2] 时贤们又另辟蹊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或从书中看到“农民革命战争的投影”,或从书中看到“新兴市民阶级的反封建要求”,或统称之为“反映并歌颂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坚决反抗的精神”。其宏文佳制,亦可谓“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确实,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论创作本旨之难求,莫过于《红楼梦》和《西游记》。其所以然,就在于它们文境恣邃,变幻纵横,意蕴富赡,都是复制了一个时代的世情小说。想用几句话去揭示他们的创作本旨,实在是难,难,难! 《镌像古本西游证道书》书影 二、玉帝、老君、佛祖对美猴王的态度 要弄清《西游记》的创作本旨,应先明确三个问题:一是,世本《西游记》署的是“华阳洞天主人校”,不是“吴承恩著”。没有华阳洞天主人的精心校饰,“秩其卷目梓之”,就没有今见百回本《西游记》。“华阳洞天”在茅山,苏轼《杨康公有石,状如醉道士,为赋此诗》记有茅君囚猴王于岩间的传说;世本《西游记》校者自号华阳洞天主人,显然是在以猴王在其掌握之中的茅君自比。二是,世本《西游记》写唐僧西行求法,事关“法轮回转,皇图永固”:象征一项了不起的事业。而没有孙悟空,唐僧到不了西天,没有观音菩萨,孙悟空不能尽其器能。校者华阳洞天主人以茅君自比,这在作品的人物中也就成了以观音自比。三是,宋元取经故事演化为世本《西游记》,实际上已成为孙悟空的英雄传奇。这位美猴王,天性洁如白玉,胆气压乎群类,又炼就“与天同寿的真功果,不死长生的大法门”,可却成日天不拘兮地不羁,而不知礼仪法度为何物,一直发展到“困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由此可见,如何对待孙悟空这一“妖仙”,便成为小说所要展示的核心问题,而华氏之意在借神魔以写人间,求索治国安邦之道的创作本旨亦寓焉! 书中描写了玉皇大帝对美猴王的态度,那就是假仁义之名而实欲弥缝禁锢之。孙悟空“强坐水宅,索兵器”,又“大闹森罗,强销名号”;东海龙王敖广和地藏王菩萨表奏玉帝,玉帝依太白金星所奏:“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与他藉名在箓,拘束此间;若受天命,后再升赏;若违天命,就此擒拿。”孙悟空当上弼马温,将天马养得肉肥膘满,但当他知道弼马温不入品,便打出南天门,回到花果山,树起“齐天大圣”旗;托塔天王并哪吒奉旨率天兵天将征剿,不期大败而归。玉帝又依太白金星所奏:“那妖猴只知出言,不知大小。欲加兵与他争斗,想一时不能收伏,反又劳师。不若万岁大舍恩慈,还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加他个空衔,有官无禄便了。”孙悟空当了齐天大圣,成日“无事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玉帝恐其闲中生事,遂令这个自幼吃桃子长大的美猴王去管那蟠桃园。这简直就像让黄鼠狼看鸡,焉有不吃之理!正是玉帝的这种欺骗、轻贤、不会用人,将孙悟空推上了大闹天宫的道路。 书中又描写了太上老君对美猴王的态度,那就是想以八卦炉中的文武火焚而化之。孙悟空搅乱了“蟠桃大会”,偷吃了玉液琼浆;误入兜率宫,又“如吃炒豆相似”偷吃了李老君五壶“九转金丹”。二郎神在李老君的协助下,擒捉了孙悟空;玉帝命押至斩妖台,将这厮碎剁其尸”。众天兵刀砍斧剁,雷打火烧,莫想伤及其身。李老君奏道:“不若与老道领去,入在八卦炉中,以文武火锻炼。炼出我的丹来,他身自为灰烬矣。”结果如何呢?炼了七七四十九天,一日开炉取丹,那钻在“巽宫”位下的美猴王看见光明,忍不住将身一纵,蹬倒八卦炉,往外就走;老君赶上抓一把,被他一摔,摔了个倒栽葱,脱身走了。这次不是回到花果山,是打上灵霄殿去夺玉皇大帝的龙位。那掉到西方路上的几块八卦炉上的砖,化为周围寸草不生的八百里火焰山。真是不仅没能降伏美猴王,反给黎元带来无穷灾难。 书中还描写了西天佛祖对美猴王的态度,那就是用“俺把你哄了”的办法将其压在五行山下。孙悟空打到灵霄殿外,玉帝忙请如来救驾。如来以打赌为名,激孙悟空跳入掌心,却将他一把抓住,指化五行山,轻轻地把他压住,山顶贴上“压贴”,书有“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并召一尊土地神祇,会同五方揭谛,居住此山监押,“但他饥时,与他铁丸子吃;渴时,与他溶化的铜汁饮”。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情节,这六字“真言”,是《西游记》杂剧里所没有的。《西游记》杂剧里是写观音从托塔天王与二郎神刀下救出,压在花果山下以待取经人。“唵、嘛、呢、叭、咪、吽”,是梵语莲花珠的译音。“我国明代民间把这句话说成‘俺把你哄了’,是当时对迷信佛教的讽刺。”[3]显然,这一情节的演化,最鲜明地反映了华阳洞天主人的创作个性。其意义则由严正而趋于滑稽,由教训而变为讽刺,明显地表露出一种对如来的不恭。 世本《西游记》如此将“五行山下定心猿”与“八卦炉中逃大圣”对举,作为孙悟空由“齐天大圣”步入“斗战胜佛”的转折点来写,这在两宋以来的取经故事中是别开生面的。它似乎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4]因为,它写孙悟空被推入八卦炉中,“将身钻在‘巽宫’位下。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得烟来,把一双眼炒红了,弄做个老害病眼,故唤作‘火眼金睛’。”可这双“火眼金睛”,使妖魔难逃其形。它写孙悟空被压于五行山下,饥餐铁丸,渴饮铜汁,鬓边少发多青草,颔下无须有绿莎,度过寒暑五百年,终于“知悔了”,愿为“法轮回转,皇图永固”而一路荡妖灭怪保唐僧西天取经。凡此,这在时人看来,就叫历尽磨难,增加了本领,增长了见识。任何人都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华阳洞天主人的思想也是如此。能将玉帝、老君、如来视为“罪恶滔天,不可名状”的“妖猴”,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英豪,已使他不失为“跅弛滑稽之雄”,说明他赏识的是孕育于个性心灵解放思潮的所谓具有“童心”的“真人”。 论者认为《西游记》歌颂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甚至认为是把他作为农民起义来歌颂的,这恐怕为华氏始料所不及。实际上,华氏歌颂的是取经路上的孙悟空,而对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只是欣赏;欣赏不等于完全肯定,而歌颂乃是最大的肯定。陈元之谓“旧序”云:“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看来,是符合华阳洞天主人思想的。所“摄心以摄魔”,就是:一方面要承认美猴王的“天不拘兮地不羁”的天性,另一方面又不可任其自然而发展为反性。所谓“摄魔以还理”,就是:一方面应该检束美猴王的身心而以免其产生不轨行为,另一方面又应该录之用之而使之能充分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造福生灵,造福社稷。足见,提出的仍然是怎样对待孙悟空,方可确保西行求法的成功,从而使“法轮回转,皇图永固”的问题。那观音与孙悟空的关系,便是华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却向来为研究者所忽略,而不知个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 滑动查看 《全像西游记》 明代杨闽斋刊本书影 三、观音对美猴王的态度 那么,作为世本《西游记》中取经队伍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观音又是怎样对待孙悟空的呢? 一曰:惜之用之。 《西游记》写“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路经流沙河,“指沙为姓”剃度了沙和尚,留作唐僧三弟子。沙和尚云:“我不是妖邪,我是灵霄殿下侍銮舆的卷帘大将。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玉帝把我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变得这般模样,又教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我胸胁百余下方回,故此这般苦恼。没奈何,饥寒难忍,三二日间,出波涛寻个行人食用。”路经福陵山,“指身为姓”剃度了猪八戒,留作唐僧二弟子。猪八戒自云:“我不是野豕,亦不是老彘,我本是天河里天蓬元帅。只因带酒戏弄嫦娥,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锤,贬下尘凡。一灵真性,竟来夺舍投胎,不期错了道路,投在个母猪胎里,变得这般模样。是我咬杀母猪,嗑死群彘,在此处占了山场,吃人度日。”路经鹰愁涧,营救了小白龙,留与唐僧做个脚力。小白龙自云:“我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我父王表奏天庭,告了忤逆。玉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诛。”路经五行山,观看帖子“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叹惜不已”,特留残步看望孙悟空。孙悟空道:“如来哄了我,把我压在此山,五百余年了,不能展挣。”并说:“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菩萨“闻得此言,满心欢喜”,遂为摩顶受戒,留作唐僧大弟子。 我们知道,《西游记》杂剧里的孙悟空并不是“灵根育孕源流出”的天产石猴,乃是吃人成性而又好色的“老猴精”。杂剧里的小白龙所以法当斩罪,并不是由于他“火烧了殿上明珠”而被其父表奏天庭“告了忤逆”,乃是由于他“行雨差迟”。杂剧里的猪八戒并不是由于“带酒戏弄嫦娥”而被“玉帝贬下尘凡”的“天蓬元帅”,乃自称是私自下凡的“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杂剧中的沙和尚所以被玉帝“贬下界来”,并不是由于他“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而是由于他“带酒思凡”。并且,猪八戒与沙和尚成为唐僧弟子也与观音不相干。凡此,也大致反映了元代取经故事中唐僧四位弟子的来历,只除猪八戒是个伪冒的金色猪。 两相对照,杂剧《西游记》既歌颂了玉帝,又歌颂了观音;而小说《西游记》却无美不归观音,无恶不归玉帝。 那么,华阳洞天主人为什么要如此独出机杼呢?孔孟讲“仁义”,如来讲“慈悲”是建筑在“佛法平等,普渡众生”基础上的。诗圣杜甫有句云:“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无疑是道出了一个客观真理。不妨活剥一下:“不过施佛法,妖魔本天神。”“俭德”者何?仁义是也,反映了诗人对苛政的憎恶,对仁政的憧憬。“佛法”者何?平等是也,反映了华氏对森严的礼法乃至对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不满。正因如此,所以《西游记》实际是“童心者自文”,是部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作品。 管仲从狱官手里被释放而提举出来,鲍叔由此而千百年来为人们传颂不已[5]。观音起用孙悟空于囚中,其胆识足可与鲍叔并驾。她对猪八戒、沙和尚、小白龙的起用,也做了唯才是宜。凡此,莫不与玉帝“轻贤”和“不会用人”形成鲜明对照。华氏这么写,不是一般地抒发怀才不遇,其中包孕着一种朦胧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封建礼法和等级秩序的对立。 二曰:束之诲之。 《西游记》里最具匠心的描写,莫过于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它也是作品中最难理解的问题之一,一般都认为作者对它是否定的。 饶有意味的是:《取经诗话》里的“隐形帽”,一变而为《西游记》杂剧里的“铁戒箍”,再变而为世德堂本《西游记》里的“紧箍”。“隐形帽”是猴行者用来帮助唐僧降伏妖魔的,而“铁戒箍”或“紧箍”却是观音用来帮助唐僧束缚孙悟空的。 《西游记》杂剧中写唐僧救了孙悟空,孙悟空却想吃唐僧:“好个胖和尚,到前面吃得我一顿饱,依旧回花果山,那里来寻我?”观音见孙悟空“凡心不退”,便降落云端,说:“通天大圣,你本是毁形灭性的;老僧救了你,今次休起凡心。我与你一个法名,是孙悟空。与你个铁戒箍,皂直裰,戒刀。铁戒箍戒你凡性,皂直裰遮你兽身,戒刀豁你之恩爱。好生跟师父去,便唤作孙行者,疾便取经,着你也求正果。玄奘,你近前来。这畜生凡心不退,但欲伤你,你念紧箍儿咒,他头上便紧,若不告饶,须臾之间,便刺死这厮。”显然,一戒其吃人,二戒其好色,这是观音给孙悟空戴上铁戒箍的目的,作者是颂扬的。 世本《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不吃人,二不好色,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那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又为什么要给他戴上个紧箍儿呢? 难道是由于他“秉性凶恶”,“全无一点慈悲好善之心”,一顿打死六个“剪径的大王”,还不受唐僧的教诲?恐怕不能这么说。孙悟空被戴上“紧箍”那天,确曾因此事与唐僧红过脸。三藏道:“你纵有手段,只可退他去便了,怎么就都打死?”悟空道:“我若不打死他,他却要打死你哩。”三藏道:“我就死,也只是一身,你却杀了他六人,如何理说?”行者道:“我老孙五百年前,据花果山称王为怪的时节,也不知打死多少人。”三藏道:“今既入了沙门,若是还象当时行凶,一味伤生,去不得西天,做不得和尚!”你想老孙可是受得闷气的?当下“按不下心头火发”道:“你既是这等,说我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不必恁般绪咶恶我,我回去便了!”撇下唐僧,一筋斗云,欲回花果山。这场争执,孙悟空固然有孙悟空的理,唐僧也是占了理的。观音曾这么说孙悟空:“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为僧,决不轻伤性命。似你有无量神通,何苦打死许多草寇!草寇虽是不良,到底是个人身,不该打死。比那妖禽怪兽、鬼魅精魔不同。那个打死,是你的功绩;这人身打死,还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自然救了你师父。据我公论,还是你的不善。”但,这只可以看做观音对孙悟空的除恶务尽思想的一种善意批评;如果把它看作观音对孙悟空戴上紧箍的原因,那就过犹不及了。观音还曾明确地告誡唐僧:“你今须是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护你,才得到灵山,见佛取经。”如何“保护”?“炼魔降怪”!无论观音,还是如来,对孙悟空勇于斗争的特点,都是肯定的。最后“功成正果”,封之为“斗战胜佛”,便是明证。只有肉眼凡胎不辨人妖的唐僧,才认为“这泼猴,凶恶太甚,不是个取经之人”。观音所以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并不是由于他“凶恶太甚”,千钧棒无情,乃是由于他虽能任劳而却不能任怨,动辄想“重整仙山,复归古洞”。这一点,书中说得一清二楚。“蛇盘山诸神暗佑,鹰愁涧意马收缰”,写孙悟空不意戴上紧箍后气得七窍生烟,闻说“菩萨来也”,便“急纵云跳到空中”对观音大叫道:“你这个七佛之师,慈悲的教主!你怎么生方法儿害我!”菩萨道:“我把你这个大胆的马流,村愚的赤尻!我倒再三尽意,度得个取经人来,叮咛教他救你性命,你怎么不来谢我活命之恩,反来与我嚷闹?”行者道:“你弄得我好哩!你既放我出来,让我逍遥自在耍子便了;你前日在海上迎着我,伤了我几句,教我来尽心竭力,伏侍唐僧便罢了;你怎么送他一顶花帽,哄我戴在头上受苦?把这个箍子长在老孙头上,又教他念一卷什么《紧箍儿咒》,着那老和尚念了又念,教我这头上疼了又疼,这不是你害我也?”菩萨笑道:“你这猴子!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系你,你又诳上欺天,知甚好歹!再似从前撞出祸来,有谁收管?—须是得这个魔头,你才肯入我瑜伽之门路哩!”彼此说得如此坦诚,哪像是“妖仙”在和菩萨说话,倒好像是两个朋友在争辩。从而也就告诉我们:束其好“逍遥自在耍子”的天性,一其心志去扫魔灭怪保唐僧求法西天,这是观音给孙悟空戴紧箍儿的主要目的。与《西游记》杂剧所写,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然而,令人难解的是,昔日观音奉旨上长安时,如来除了取出“锦襕袈裟”一领,“九环锡杖”一根,嘱咐菩萨“与那取经人亲用”以外,又取出“三个箍儿”递与菩萨道:“此宝唤做‘紧箍儿’,虽是一样三个,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紧禁’的咒语三篇。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他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儿与他戴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观音后来将“锦襕袈裟”和“九环锡杖”给了唐僧,“紧箍儿”给了孙悟空,“禁箍儿”给了熊罴怪,“金箍儿”给了红孩儿;而熊罴怪和红孩儿却不是唐僧的徒弟,猪八戒与沙和尚是唐僧的徒弟反倒没给,二人又皆曾“血人为饮肝人食”。这是怎么回事呢?至少可作三种解释: 一是,世德堂本祖本作者的疏忽,华阳洞天主人改定时又没有注意。 二是,世德堂本祖本的作者为了突出三藏作为“圣僧”的地位,写观音按如来法旨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人各戴一戒箍,三藏由于会念“金紧禁”三咒而使他们不敢不伏使唤。华阳洞天主人为突出孙悟空的地位,并为了增强唐僧师徒四众之间的喜剧性,改写了有关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将禁箍儿与了熊罴怪,金箍儿与红孩儿,却由于疏忽而没有对如来的法旨作相应的修改。其情况,犹如删净了花果山自在为王时期孙悟空好吃人肉的情节,却由于疏忽而没有对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中的一段话,即孙悟空对唐僧说:“老孙在水帘洞里做妖魔时,若想人肉吃”云云作相应的改变。 三是,世德堂本这种将猪八戒、沙和尚之戒箍戴到熊罴怪、红孩儿头上,却又未对观音奉旨上长安时所领如来法旨作相应的修改,不是由于华阳洞天主人的疏忽,他是自知的,强意识的。其情况,犹如割断了西行路上的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王﹑狨王”等作相应的修改,但又留下牛魔王与孙悟空的结义关系与此相呼应。其用意,显然是要写出观音上长安虽则是奉佛旨,但寻谁作取经人,用谁作弟子一路保驾,与谁戴上戒箍,却并非唯如来法旨是从,乃是凭慧眼与按实际需要。从而也就既突出了孙悟空的地位,又突出了观音菩萨的作用。 哪种解释为是呢?一则今见材料太少,二则未见高明论说,三则问题似小实大,笔者不敢强作解人。如果一定要我交份试卷,那我认为这三种解释的可能性是递增的。因为,后者最符合陈元之序中所说的“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质之高明,不知以为何如? 一来由于唐僧不念“紧箍咒”则已,一念“紧箍咒”便变得对敌慈悲对友刁,致使孙悟空曾噙泪跪求观音:“万望菩萨,含大慈悲,将《松箍儿咒》念念,褪下金箍,交还与你,放我仍往水帘洞逃生去罢!”二来由于孙悟空是华氏讴歌的英雄、心爱的主人公,他与华氏的是非观念总体上是一致的,所以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华氏对观音给悟空戴紧箍儿,是否定的。我以为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要知道,熊罴怪戴上禁箍儿成了落伽山守山大神,红孩儿戴上金箍儿成了紫竹林善财童子;孙悟空对他们俱成正果是肯定的,而这一肯定显然反映了华氏对观音如何用“箍”的肯定。诚然,作品结尾,写孙悟空已封为“斗战胜佛”,其最后一句话是向唐僧说的:“师父,此时我已成佛,与你一般,莫成还戴金箍儿,你还念甚么《紧箍咒》掯勒我?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想到头上的紧箍儿,还是那么忿忿不平。然而,此时已封为“旃檀功德佛”的唐僧又是怎么回答的呢?“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孙悟空“举手去摸一摸,果然无之。”三藏这一段话显然也是华氏的结论。由此可见,华阳洞天主人对观音与孙悟空戴紧箍儿是肯定的,否定的只是肉眼凡胎的唐僧乱念《紧箍儿咒》。 三曰:勉之助之。 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孙悟空,当他头戴紧箍认真踏上征程时也曾临事而惧,扯住菩萨不放道:“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西方路这等崎岖,保这个凡僧,几时得到?似这等多磨多折,老孙的性命也难全,如何成得甚么功果!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菩萨道:“你当时未成人道,且肯尽心修悟;你今日脱了天灾,怎么倒生懒惰?我门中以寂灭成真,须是要信心正果;假若到了那伤身苦磨之处,我许你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十分再到那难脱之际,我也亲来救你。你过来,我再赠你一般本事。”菩萨将杨柳叶儿,摘下三个,放在行者的脑后,喝声“变!”即变做三根救命的毫毛,教他:“若到那无济无主的时节,可以随机应变,救得你急苦之灾。”真是惠诲谆谆,是开导,也是承诺。行者“闻了这许多好言,才谢了大慈大悲的菩萨。” 作为取经人精神上的领袖和事实上的组织者,观音菩萨对孙悟空的这种开导和承诺,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它使孙悟空一路炼魔降怪增加了信心,也为唐僧西游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孙悟空是聪明的,他接受了观音的教诲,并相信观音不会失信于人。唐僧的《紧箍儿咒》是观音传授的,但你几曾见过观音对孙悟空念过那玩意?华阳洞天主人令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黑风山、五庄观、枯松涧、通天河,若非观音亲临,唐僧师徒不能释厄;狮驼洞,若非那“三根救命毫毛”,孙悟空逃不出鹏魔王的“阴阳二气瓶”。如此劳心劳力护法取经者,甚至“未及梳妆”便纵上祥云赶去救难,这样的菩萨又怎能不使“有仁有义的猴王”感服而“至心朝礼”呢! 四曰:谅之容之。 有容德乃大,无欲志则刚。一用以说观音,一用以说孙悟空,我以为是合适的。无孙悟空,唐僧到不了西天;无观音菩萨,孙悟空不能尽其器能。“那猴头,专倚自强,那肯称赞别人?”反映为平生喜笑悲歌气傲然。这也见之于他对唐僧顶礼膜拜的观音菩萨的态度,尽管观音是他心目中最为可敬可亲的人。明明是他大胆,将“锦襕袈裟”卖弄,拿与小人看见,却又行凶,唤风纵火,烧了观音的留云下院;反而到落伽山紫竹林放刁,说:“我师父路遇你的禅院,你受了人间香火,容一个黑熊精在那里邻住,着他偷了我师父袈裟,屡次取讨不与,今特来问你要的。”甚至还诅咒观音:‘该她一世无夫”;奚落如来,说他是“妖精的外甥”。这实在有点不恭,罪当入阿鼻地狱。可观音却谅之容之,纵然骂他“泼猴”,也充满着爱心。 孙悟空还好与观音菩萨说嘴,观音菩萨亦喜与猴王说笑:“悟空,我这瓶中甘露水浆,比那龙王的私雨不同:能灭那妖精的三昧。待要与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须是留些什么东西作当。”行者道:“可怜!菩萨这等多心。我弟子自秉沙门,一向不干那样事了。你教我留些当头,却将何物?我身上这件绵布直裰,还是你老人家赐的。这条虎皮裙子,能值几个铜钱?这根铁棒,早晚却要护身。但只是头上这个箍儿,是个金的,却又被你弄了个方法儿长在我头上,取不下来。你今要当头,情愿将此为当。你念个《松箍儿咒》,将此除去罢;不然,将何物为当?”这是观音起程降伏红孩儿时与孙悟空的言笑。它是灵霄殿上玉帝和仙卿间所不可能的。写出了观音和孙悟空关系的融洽,也反映了华氏的人伦理想。 正如恩格斯所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6]世本《西游记》的主要特点,是寓庄于谐,借神魔以写人间,在幻想中求索治国安邦之道。如果说,观音是笑花主人所欲看到的具有“常心”的“常人”[7]的典型,即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人物,那么,孙悟空则是李贽所欲看到的具有“童心”的“真人”[8]的典型,即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人物。二者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反映着华氏世界观矛盾着的两个侧面。这就是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观音实际都是“华阳洞天主人”幻想中的自我——当他呼唤“伯乐”,则幻想中出现了观音;当他寻找“千里马”,则幻想中出现了孙悟空。二者相辅相成,从中表现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期望孙悟空的人才能遇观音式的人物获得起用,并通力合作,扫灭社会一切邪恶势力以造福生灵、造福社稷。把孙悟空说成“农民起义的英雄”,甚至将观音也推到孙悟空的对立面,以此去探求作品的创作本身,窃以为只能是南辕北辙,因为这不符合作品的实际。 滑动查看 《西游证道书》康熙间刻本 四、天下治乱,系于用人 综上所述,则不难看出:《西游记》是部寓庄于谐、借神魔以写人间百态的文学巨著。它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治平人才以及如何对待这类人才问题。认为道学之中已几无治平之人,期望能有观音式的人物去发现并起用孙悟空式的人物,以扫荡社会邪恶势力,共建玉华国式的王道乐土,这便是作者的创作本旨。 那么,对作者的这一创作本旨,又该作何历史评价呢? 如果说,孙悟空是具有“童心”的“真人”中的英雄,亦即新兴市民阶层的智慧和力量的集中体现者和代表,那么,观音则是具有“常心”的“常人”中的哲人,亦即地主阶级正统派中有思想头脑和政治头脑的开明人士。一方面把“法轮回转,皇图永固”的希望,不是寄托在如唐僧式的具有“常心”的“常人”身上,而是寄托在如孙悟空式的具有“童心”的“真人”身上;另一方面,却又对具有“常心”的“常人”中的某些代表人物抱着幻想,并要求具有“童心”的“真人”须检束自己的身心以服从大局。一方面,在时代精神的呼召下,情不自禁地去为新兴市民阶层要求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识作辩护,去为新兴市民阶层的社会力量争地盘;另一方面,又在历史惰力的牵制下,不能自已地想把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力量在总体上纳入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轨道,甚至给孙悟空戴上紧箍以使其个性心灵的解放不越孟子仁政思想的雷池。凡此,也就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反封建的斗争性和妥协性。因此,也就形成了作品创作主旨的历史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 然而,“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最为重要的是,假若没有“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第二代狂人贾宝玉形象,假若没有《西游记》中的儒释道三教的种种不恭,便不会有《红楼梦》中对儒释道三教的全面怀疑。所以,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9]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需补充一句:这种打破实始于《西游记》而成于《红楼梦》。其写法的打破,将于下章论说。其思想上的打破可见一斑。 假若以一句话来对《西游记》的思想价值作结,那我以为最恰当不过的,当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西游记》是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文艺开山作。 注释 [1]《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2]《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3]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西游记》第七回注。 [4]《孟子·告子章句下》。 [5]《孟子·告子章句下》。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至页。 [7]《今古奇观》序。 [8]李贽:《焚书·童心说》。 [9]《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载张锦池先生《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第六章,人民文学出版社年8月版。 作者简介 张锦池先生(.2~.9),江苏靖江人。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哈尔滨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长期担任该学科带头人。撰有论文数十篇,著有《红楼十二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西游记考论》《西游记导读》《水浒传考论》《三国演义考论》等。 欢迎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ongtongzia.com/xtzyh/5544.html
- 上一篇文章: 盛唐瑰宝丝路奇珍海兽葡萄镜撷萃北京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