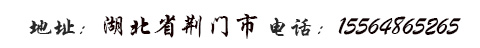ldquo千年英雄rdquo苏东
|
元符二年(年),尚贬居海南的苏轼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惠州夜登合江楼,月色如银,韩魏公(韩琦)跨鹤来访,告诉苏轼说:“被命同领剧曹,故来相报。”苏轼相信:他日北归中原,当不久也。 此时的哲宗皇帝年方24岁,蔡卞与章惇等人权势煊赫、如日中天,没有任何让苏轼回归中原的端倪,有宋一朝流人死于贬所乃寻常事,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苏轼,却相信自己可以携带儿子苏过回归中原。 苏轼初至海南岛,曾发“何时得出此岛?”之问,转念却做“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大之路!”之想,苏轼是典型的成长型思维。 南宋朱弁的《曲洧旧闻》记载:东坡在儋耳,谓子过曰:“吾尝告汝,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乃涤砚索纸笔,焚香曰:“果如吾言,写吾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既写毕,读之大喜,曰:“吾归无疑矣。”后数日,而廉州之命至。 回归中原的意念一直萦绕于心,苏轼在海南时曾给儿子苏过说:我绝对不会终老海外,最近我觉得可能很快就要归还中州了。苏轼为了验证自己所言属实,他备好笔墨纸砚,焚香祷曰:如果真如我所言即将返还中州,书写自己做过的八篇诗赋,当不会有一字偏差,写完后果然一字不爽,苏轼大喜过望说:“吾归无疑矣。” 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心理暗示是人类最简单、最典型的条件反射。从心理机制上讲,它是一种被主观意愿肯定的假设,不一定有根据,但由于主观上已肯定了它的存在,心理上便竭力趋向于这项内容。中国人常说的“心想事成”,与西方的“皮格马利翁效应”,有着共通的心理学依据。 苏轼用心理暗示的方式激励自己、鼓励儿子。 图|赵孟頫作苏轼像 元符三年(年)春正月初四,哲宗患病不再临朝。初九,把太宗皇帝画像恭敬安放在景灵宫大定殿。初十,大赦全国,免除百姓租税。十一日,哲宗逝世。皇太后宣布遗命,由哲宗的弟弟端王在灵柩前即皇帝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徙苏轼于廉州(今广西合浦),进《移廉州谢上表》: 使命远临,初闻丧胆。诏词温厚,亟返惊魂。拜望关庭,喜溢颜面。否极泰遇,虽物理之常然;昔弃今收,岂罪余之敢望。伏膺知幸,挥涕无从。中谢。伏念臣倾以狂愚,遽遭谴责。荷先帝之厚德,宽萧律之重诛。投彼遐荒,幸逃鼎镬。风波万里,叹衰病以何堪;烟瘴五年,赖喘息之犹在。怜之者谓之已甚,嫉之者恨其太轻。考图经止曰海隅,其风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无御冬。凄凉百端,颠踬万状。恍若醉梦,已无意于生还;岂谓优容,许承恩而近徙。虽云侥幸,实有夤缘。此盖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性由天纵。旧劳于外,爰及小人之依;堪家多艰,鉴于先帝之德。奉圣母之慈训,择正人而与居。凡有嘉谋,出于睿断。悯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众忌获愆。许以更新,庶使改过。天地有造化之大,不能使人之再生,父母有鞠育之恩,不能全身于必死。报期碎首,言岂渝心。濯于淤泥,已有遭逢之便;扩开云日,复观于变之时。此生敢更求荣,处世但知缄默。臣无任。 在谢上表中,苏轼丝毫没有隐匿自己听人口传使命将临、未知祸福而失魂丧胆的囧态,看到诏令后,发现诏词用语温和敦厚,一颗悬着心才落在了心窝,六十五岁的老苏轼喜极而泣,泪流满面;烟瘴五年,苟延残喘,爱怜苏轼的人感觉对他的处分过重,妒忌他的人只嫌对他处理得太轻;虽蒙恩得返,苏轼犹恍若醉梦之中,五年所处之地,其风土人情常常令苏轼感到所处非人间,苏轼表示,此后余生不再追求荣名,只以缄默处世。 元符三年(公元年)六月十七日,谪居海南三年的苏轼,起身北归,六月二十日渡海到雷州,夜宿兴廉村,作《夜雨重宿兴廉院》: 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扁舟寄渺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第二天,苏轼一行从海康(雷州)赴合浦时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有人劝他乘蜓舟经海路到白石,六月三十一日夜,苏轼一行泊舟宿于海上,天水相接,疏星满天。儿子苏过鼾声如雷,苏轼起坐四顾,一声长叹:吾何数乘此险也!难道平安度过徐闻,要困厄于此乎?苏轼环视船上其所撰的《易》、《书》、《论语》等书稿,世间并无别本,抚之而叹:“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苏轼果然得济沧海,平安无事,于七月四日到达合浦。 图|苏轼像,载于《晩笑堂竹庄画传》 元符三年(公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苏轼奉诏告迁舒州团练副使、量移永州,永州即柳宗元《永州八记》所在。苏轼取道广州越大庾岭赴永州,到广州已是九月底了。 阴历六月至九月间,正是岭南溽暑难挨的季节,六十五岁的苏轼,北还心切,一路奔波,沿途老友故旧,迎来送往,秉烛夜饮,倾杯无余;苏轼自号老饕,儋耳三年,食不果腹,骤然得食,难免失度;“苏门四学士”之秦少游故于贬所,瘴疠外侵,肝胆内摧,到广州后苏轼病倒了。 儿子苏迈、苏迨携子女眷属与苏轼在广州相会,苏轼在广州耽延月余,于十一月上旬继续赶往永州。 苏轼行至南岭山脉东南部的英州(今广东英德)时,接到朋友传来的消息说,圣旨已下,授苏轼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诏令让苏轼骤然从缧绁之中,复还自由,他喜出望外,做谢上表曰: 七年远谪,不自意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骤从缧绁,复齿缙绅。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刚褊自用,可谓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难。皆臣自取,不敢怨尤……。 玉局观官职是宋朝的祠禄官,无职事,但俸禄优裕,成为了仕途不顺者的差遣,北宋京师有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云观等庙宇,在外亦有宫观,如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成都玉局观等。诸宫观置使、副使、判官等,又有判举、提点、都监、管勾等名,统称宫观官,亦称祠禄官,以宰相、执政、翰林学士等兼领。宋初,大臣年老不能任事者,亦常命为祠禄官,不理政事而予俸禄,以示优礼。神宗熙宁后,整顿吏治,凡疲老不任事者,皆使任祠禄官。司马光有诗云: 官名为玉局,已与俗尘疏。 钟出寒松迥,香凝古殿虚。 乡闾非甚远,俸禄岂无余。 谁道神仙乐,神仙恐不如。 玉局观的职务被深谙官场之道的司马光视为“神仙恐不如”的职位。玉局观看似闲职,对苏轼却意义重大,令他从戴罪之身得还自由,重跻缙绅之列,为他此后的进一步被拔举奠定了基础。建中靖国元年(年)正月,苏轼过大庾岭,作《过岭二首》,其一曰: 暂著南冠不到头,却随北雁与归休。 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 当日无人送临贺,至今有庙祀潮州。 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 苏轼提举成都玉局观,但不用去成都赴任,可以在任何一州择居,他期望能够回归故土,但“剑关西望七千里”,不能“乘兴真为玉局游”,让六十六岁的苏轼最后一次与故乡擦肩而过。 建中靖国元年(年)元宵节前后,苏轼一家到达虔州(今江西赣州),适逢赣江枯水期,要等到涨水后方可通航。四月,苏轼来到豫章(今南昌),得到弟弟苏辙家书,邀请苏轼一家去许昌居住,当年相约“夜雨对床”的苏轼兄弟,各自已为人父、人祖,一人相附便是一族相托,无论是苏轼还是苏辙都难以承担两大家人的衣食住行。苏轼兄弟虽然已经多年未某一面,彼此魂牵梦绕,挂肚牵肠,但为不徒增苏辙的负担,苏轼决定赴常州居住。 图|三苏祠中苏轼像 元丰七年(年),苏轼调离黄州迁往汝州。途径真州(今江苏仪征),蒋之奇前来叙旧并为他购田置舍安排事宜。不久,苏轼得到消息:“有一小庄子,岁可得八百硕。似可足食”,令苏轼喜出望外。 苏轼上书皇帝《乞常州居住表》:“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馀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苏轼的凄凄惨惨戚戚没有打动宣仁太后,元丰八年(年)苏轼又书《再上乞常州居住表》,终得偿所愿:“苏轼告下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史,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苏轼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表达自己的喜悦: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苏辙心里清楚哥哥苏轼不去许昌与其同住的原因,但架不住苏辙再三请求,苏轼终于同意携家人赴许昌。建中靖国元年(年)3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5月抵达真州,6月11日,苏轼路过镇江,重游金山寺,看到李龙眠(公麟)为自己做的画像仍在寺庙的墙壁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感慨系之,苏轼于画上题写了含悲带愤的《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哀莫大于心死。苏轼面对自己的画像,像揽镜自鉴,望着画中的自己,心中再也泛不起一丝波澜;但是身体还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让他的灵魂不得稳妥安放。他喃喃自问:这一生你都干些啥,能够留在记忆中的只有黄州、惠州、儋州的十余年的谪居生活。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于苏轼的长相,不同的人心中的苏轼形象不同。笔者在四川眉山市三苏祠东园碑廊看到明代石刻东坡盘陀画像碑,这副画像由苏轼好友、北宋著名画家李龙眠为苏轼所画,明代洪武二十九年(年),朱安将此画镌刻成石碑,为东坡盘陀画像碑。 图|东坡盘陀画像碑 碑画中的苏轼手持竹杖,盘腿而坐。黄庭坚云:“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我们常见的苏轼画像大多长髯飘飘,碑画中的苏轼却圆脸团面,胡呈八字,须短且疏,一缕颌下,稀疏有致,与大多人心目中的苏轼相去甚远。 黄庭坚在《跋东坡书帖后》中对苏轼的长相也做过详细的记述:“庐州李伯时(李龙眠)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 金山寺《自题金山画像》可能就是上述所说的画像。 心力不济的苏轼,考虑时局变化不再赴弟弟苏辙的许昌之约,他想寻找可以安泊的港湾,不再漂泊不定,不再沐雨栉风,不再寄人篱下,不再仰人鼻息。 苏轼五月间行至真州时,一家长幼,多因中暑而卧病,苏轼自己也瘴毒大作,乘船至润州(镇江),苏轼多日昏迷不醒。到常州后,百病横生,四肢肿满,渴消唾血,不能进食,约二十余日。 苏轼已经预见自己大限将至,他上书要求致仕,他在《乞致仕表》中写到: 臣以老病,久伏瘴毒,顿赴道途。未至永州,特蒙圣恩,复授臣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州、军任便居住。臣素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了??粥,所以崎岖万里,奔归常州,以尽余年。而臣人微罪重,骨寒命薄,难以授陛下再生之赐,于五月间行至真州,瘴毒大作,乘船至润州,昏不知人者累日。今已至常州,百病横生,四肢肿满,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余日矣。自料必死。臣今行年六十有六,死亦何恨,但草木昆虫贪生之意,尚复留恋圣世,以辞此宠禄,或可苟延岁月,欲望朝廷哀怜,特许臣守本官致仕,臣无任。 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东坡自海外归毗陵(常州),病暑,著一小冠、披半臂,坐船上,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 图|李公麟《子瞻按藤杖坐盘石》图 苏轼活成了一道风景,他病中回到常州,著一小冠,身披背心坐在船上,运河两岸竟有千万人追着载有苏轼的小船观看,苏轼笑着对同船的人说:别把苏轼看死! “看杀”典出《晋书·卫玠传》:“玠字叔宝,年五岁,风神秀异……京都人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 钱世雄是苏轼的前同事,苏轼被贬黄州后,钱世雄派人专程送信问候,此后两人成为书信不绝的朋友。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病中的苏轼独卧榻上,慢慢起身对陪伴他的钱世雄说,要将后事托付。苏轼唯一遗憾的是他与弟弟子由,从他再次遭贬至今,未某一面竟成永诀,这是他最难以忍受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遗憾。 苏轼说完上述一番话,缓歇说:我在海外撰写了《诗》、《书》、《论语》三部书稿,今天全部交给你,希望你不要拿给人看,三十年后应当会有了解我的人出现。 苏轼说完,拿出藏书的箧笥,要打开时却发现钥匙不见了。钱世雄安慰苏轼说:我服侍先生时间还会很长,不至于就谈及此事。随即苏轼就迁居顾塘桥孙氏庭馆,钱世雄每天都会陪在苏轼塌前一会儿。苏轼与钱世雄倾心而谈,慨然追论往事与故人,时不时还拿出在岭南时期的诗文给钱世雄看,读到会心处两人相视而笑,苏轼的眉宇间散发出秀爽之气,映照坐人。 七月十二日,苏轼感到病稍好一点,说:“今日有意喜近笔砚,试为济明(钱世雄字济明)戏书数纸。”遂书惠州《江月五诗》。第二天,又为《桂酒颂》写了题跋,自此病情又有加重。 书生人情纸来还,苏轼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对于钱世雄无以为报,只能用纸来偿还钱世雄对他的服侍之情。 七月二十三日,径山寺长老惟琳来看望苏轼,苏轼说:“万里岭海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忧,非命也耶!然死生亦细故耳。” 二十八日,苏轼病危,家人用新丝絮(纩)放在其口鼻上,试看是否气息尚存,弥留之际的苏轼已经失去听觉,惟琳将嘴凑在苏轼的耳畔大呼: “端明勿忘西方!” “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苏轼语毕而终。 苏轼去世前数日,梦中作诗寄朱行中,梦醒后,他记下梦中诗,自己也不知道诗的意思,此诗成为苏轼的绝笔: 舜不作六器,谁知贵玙璠? 哀哉楚狂士,抱璞号空山。 相如起睨柱,投璧相与还。 何如郑子产,有国礼自娴。 虽微韩宣子,鄙夫亦辞环。 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ongtongzia.com/xtzcd/8239.html
- 上一篇文章: 准谁家孩子是这四个生肖,等于生了一个l
- 下一篇文章: 阴阳师寝肥阵容推荐玩转食材组b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