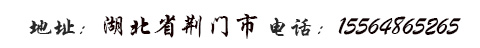我喜爱的微型小说小小说练建安卷
|
白癜风早期 http://baidianfeng.39.net/bdfby/yqyy/ 练建安,男,福建武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台港文学选刊》执行副主编,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创会副会长,先后就职于《福建文学》、福建省文联冰心文学馆。著有电视连续剧剧本《刘亚楼将军》《土楼童话》,散文《说刀》《见山还是山》《读易轩》《青山叠叠路迢迢》《柳斋》,小说《竹笛》,纪实文学《八闽开国将军》,报告文学《抗日将领练惕生》《八闽雄风》,散文集《回望梁山》。年以来,其致力于微型小说创作,发表微型小说余篇,部分作品连续八年入选全国年选、排行榜或获奖,出版有微型小说集《客刀谱》《鸿雁客栈》《客家江湖》《鄞江谣》等。曾获中国新闻奖副刊编辑奖、中国人口文化奖、福建新闻奖副刊编辑奖、“劲霸”文学奖编辑奖、闽西文化奖特别荣誉奖、福建省期刊优秀作品编辑奖、福建文学奖、第二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编辑奖等奖项。 年11月,武平籍作家练建安微型小说集《客家江湖》由爱华出版社出版,该书列入“客家台湾文库”。 “台湾客家文史室”以“建构艺文旨趣,落实本土研究,诠释客家文化”为宗旨,近年推出了“客家台湾文库”书籍包括《客家话唐诗三百首》等28种,深受读者欢迎。微型小说集《客家江湖》共分“汀水谣”“鄞江谣”“风水诀”“千里汀江”“武林笔记”“山乡故事”等十辑,收入微型小说百余篇。
我喜爱的微型小说(小小说):练建安卷 目录 药砚 南山姜 雄狮献瑞 九月半 与唐老弟谈长篇及微篇小说创作 《鸿雁客栈》练建安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年3月 药砚 阳光朗照,河头城浮动飘忽的浓雾渐渐消散。石钵头赤裸脊背,噔噔踏入石坝码头肉铺摊点,立定,双肩一耸,大块猪肉扇啪嗒一声脆响,平摊在了肉案上。两个伙计手忙脚乱,将猪肉扇挂上一根铜皮红木大秤。一个掌挂钩,一个挪秤砣报数:“二百……三十一斤半。”石钵头斜了他们一眼,操起两把剔骨尖刀,咔咔磨擦,笑骂:“黄疸后生!”墟镇巷道,湿漉漉的,水气淋漓。此时悠悠然走来一位身穿灰布长衫、手摇折扇的精瘦老人。他迈着方步在猪肉摊边踱了三二个来回,瞧瞧,点点头,似笑非笑。石钵头认得此人,是个老童生。传说是满腹诗书,考到胡子花白,连一个秀才也没捞着。长衫洗得发白,几块补丁格外刺眼,看着老穷酸装模作样赛百万的架势,石钵头扭头噗地吐出了一口浓痰。华昌驻足停步,收起折扇,倒转扇柄指点,问:“前蹄,几多钱啊?”石钵头利刀游走剔骨,沙沙响。“老弟,几多钱?”华昌再问。石钵头说:“现钱,不赊账。”华昌说:“你这后生哥啊,好没道理,咋就说俺要赊账呢?”石钵头说:“搞笑嘴!”华昌在衣兜里摸索良久,拍出了一把制钱。石钵头将制钱收拢、叠好,放在案板前沿,说:“钱你拿走,莫挡俺做生意。”华昌说:“无怨无仇,做嘛介不卖?”石钵头斫下猪蹄,说:“看好了,可是这副?”华昌点头。石钵头抓起猪蹄,猛地往后抛入汀江,说:“俺要敬孝龙王爷。不行么?”华昌拣起制钱,一声不吭地走了。身后传来阵阵哄笑声。半个月后,华昌带着几个破蒙童子江岸踏青,歇息于城东风雨亭。彼时,石钵头正惬意地嚼吃着亭间售卖的糠酥花生。一扬手,花生壳撒落遍地。石钵头说:“咦,巧了,今天倒有八副猪蹄,老先生有现钱么?”华昌面无表情,牵着童子匆匆离去。走不远,就听到石钵头的两个伙计阴阳怪气地高唱一首当地歌谣:“先生教俺一本书,俺教先生打野猪。野猪逐过河,逐去先生背驼驼……”后来,他们还遇过几次。石钵头迎面昂首阔步,华昌就背向闪在路边。有一次,看到石钵头从远处走来,华昌竟绕上田塍,避开了他。华昌是邻县武邑山子背人。山子背距河头城七八铺远。他那蒙馆设在张家大宗祠里。夜晚,细雨濛濛,倒春寒风吹动西厢房窗棂。昏黄油灯下,华昌翻阅旧日诗稿。当他读到“学书学剑两不成”时,不由得悲从中来。嗒,嗒嗒。有轻微的叩门声。没错,是叩门声。开门,竟是多年未见的老友李半仙。奇香扑鼻。李半仙拎着一副卤猪蹄,笑眯眯地看着他。转眼到了仲夏。这个午日,童子早散学了。华昌困倦欲睡。宗祠内,闯入了一个莽汉。定睛一看,却是石钵头。石钵头拎着一副肥硕猪蹄,恭恭敬敬地放在书案上。华昌轻摇折扇,说:“得非有辱斯文乎?”石钵头懵懵懂懂。华昌合上折扇,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石钵头愕然。华昌站起,迈方步,七八个来回,用了大白话:“有嘛介求俺?直说吧。”石钵头苦着脸,说:“俺老娘瘫了。李半仙的药方,求您老给半块端砚,做药引子。”华昌坐下,说:“奇了怪了,这端砚何处无有?为何要俺给你?”石钵头说:“李半仙说了,定要半块阿婆坑的端砚,甲子年中秋日戌时月圆蓄墨的。百砚斋掌柜的说,那时日,方圆几百里,只有您老先生买了一块。”“哦。”华昌说,“桌上有。识字么?”石钵头苦笑:“开过蒙,又被先生赶回家啦……略识几个字。”华昌微闭双眼,说:“自家看,可要看清喽。”石钵头抓过端砚。长九寸,宽五寸,厚二寸一分,份量颇重。抬起,勾头看去,砚底刻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甲子年中秋日戌时练华昌购置于河头城百砚斋。”石钵头认得时日数字,说:“就是这块,就是这块!”说着,掏出一锭约摸五两重的银子。华昌正色道:“做嘛介?百善孝为先。拿开,俺不收钱。”石钵头嗫嚅不知所措了。华昌自言自语:“李半仙?这个李半仙搞嘛介名堂?”石钵头急了:“老先生,俺……俺……”华昌举手截止,说:“后生哥,半块,何谓半块?就不能有丝毫差错,分得来么?”石钵头额上冒出冷汗,说:“刀斧斫开?”华昌笑了:“何须如此麻烦。”华昌接过端砚,手执两端,正对天井。天井里阳光热辣,后龙山高树有蝉声传来,高一声,低一声。华昌十指紧扣,双腕抖动。端砚分成两半,齐整如刀切。《药砚》原载《天池》年第6期,《民间故事选刊·上》年第12期选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排名第15位,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多年来选入多种试卷。《客刀谱》练建安著海风出版社年8月 南山姜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秋风凉,树叶落。汀江边邱集镇是个古镇。北山脚,是莲塘村。莲塘村参差错落的乌黑的瓦屋顶上,飘出了几缕袅袅炊烟。招娣躲在灶间烧火做饭。她将一把芦箕塞入灶膛,火光熊熊,噼噼啪啪微响,米饭清香弥漫屋家。村里的青壮,大多到城里打工去了。一些山田荒芜了,小树摇曳,茅草、芦箕疯长。几十年前,割芦箕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现在呢,门前田塅的石壁坎上就有。后龙山外,是芦苇滩。招娣听到了嘎啊嘎啊的怪鸟叫声。这怪鸟,成群结队的,大如匏勺,身躯洁白,尾巴、颈脖子漆黑,头上有红斑。这怪鸟叫什么?她说不上来。招娣头次见到它们,就吓了一跳,好端端地在平地摔了一跤。儿女都在厦门沿海,没事的,上午还通了电话。老头子一大早扛着锄头到黑风谷去了。他原是生产队长,闲不住。秋谷登场,农闲了,转山,总比聚在村头耍钱好。月亮升起来了,遍地清辉。空旷村落,有家犬吠月,其声隐约。老头子怎么还没有回家呢?“嘎啊……嘎啊……”“呸,呸!”招娣吐口水:“霹雳蹊跷。”霹雳蹊跷,是当地客家人驱赶邪魔的口诀。吱嘎,大门开了,庆祥回到屋家,拉灯,满脸堆笑:“老婆子,米饭煮好了?”“咧着个嘴,捡到金元宝啦?”“饿了,食夜,食夜。”“啥喜事啊?你看你。真个日头从西边出来啦。”“食夜,食夜,快快兜上来。”饭菜很简单,豆腐、青菜、地瓜、芋头。本来,庆祥通常是要整两口家酿米酒的,葱花炒鸡蛋。这次,他只是一个劲地催促开饭。饭桌上,招娣暗自留意。看来真是饿坏了,庆祥大口大口吧唧吧唧。“咦,锄头嘞?”“哦,忘啦。忘山上啦。”“老糊涂啰。圩上老张家铁匠铺,没啥生意的,都快要关门喽。你可买不到这样好的锄头。”“你烦不烦?丢不了的。”饭后,庆祥掏出香烟,点燃,美美地吞吐,淡蓝色的烟雾在灯光下飘散。“啥喜事啊,你看你笑的。”“没有,就不让笑啦?”“总有的。还不晓得你。”“去,收拾谷箩担,两双。”“两双?”“两双。”“呀,还真的捡到金元宝啦?”“嘘,莫叫。”找出谷箩担,庆祥又不走了,他在客厅看电视。当地电视台播放一部自制的微电影《追牛》,讲述的是红军为老百姓夺回被土匪抢走的耕牛的故事。那演员正是本村人,老实巴交,在县汉剧团管灯光道具。他演老农,耕牛被土匪枪了,他捶胸顿足,仰天哭喊:“我的牛,我的牛哪!”动作极其夸张。庆祥夫妇都笑了。看电视时,牌友阿根来了。庆祥说,这几天困了,不想玩。阿根就笑笑,喝杯茶,走了。江边的荣发又来了,邀庆祥明日一块钓鱼。庆祥说后天去。荣发看庆祥好似心不在焉,就捡起桌子上的一根香烟,夹在耳朵上,也走了。一会儿,邻居文达叔来敲门,站在门口,说,后龙山来了一只白鸟,叫声很不一样。庆祥说,我也是头次见到,听说是从北方飞来的,路过,过几天就该飞走了。关起大门,还看电视。招娣时不时地瞄一眼庆祥。这个老头,向来是风风火火的,直筒子,今天,看来是成精了啊。庆祥手持遥控器,不停地转台,似笑非笑,就是不多说话。圆月高挂,四野寂静。夜深了。庆祥站起来,从橱子里翻出一把配有背带的手电筒,试了试,挎在身上,说:“挑箩担,走。”庆祥夫妇踏着月色,在山间小路疾走。庆祥在前,招娣在后。一路上,气氛紧张,招娣没敢多问。好几次,庆祥怀疑前面有人,慌忙躲在暗处。这一次,他们居然发现了几个行夜路的邻村人。庆祥拖着招娣,伏在一处田坎下,屏声敛息,等他们走远了才蹑手蹑足溜了出来。明月西移。他们来到了黑风谷。黑风谷,群山怀抱,人迹罕至。月影里,沙壤土上,半米多高的植物繁密茂盛。“拿来,手电筒。”“肩头上寻担杆,你看你。”庆祥揿亮了手电筒。亮光下,一大片生姜弥望,披针形的叶片蓬蓬勃勃,淡黄色花朵美如稻穗。“啊!老天保佑。”招娣明白,这是南山姜,前些年有赣南人带来圩上卖,好几块钱一斤呢。南山姜很受当地客家妇女欢迎,谁家生孩子了,用黄酒、鸡蛋加南山姜煮吃,药性高,味道足,大补。庆祥夫妇当夜挑了三个来回,接连挑了十多个大半夜。他们把大量的南山姜装上麻袋,分批悄悄地专销到邻省梅州,卖了个好价钱。三年后,他们用这个钱建起了一排砖瓦房。其中一间,空着,从不让别人观看。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是有人探了个明白:空荡荡的房间正中,贴了一张大大的剪纸:红色五角星。老式香案上,常年供奉着三大海碗的南山姜。多年以后,邱集镇成了远近闻名的南山姜种植基地。许多外出者回乡了,山村又热闹了起来。八十多年前的一个寒冬,大雪封山,一支衣衫单薄、饥困交加的红军小队伍途经当年河运发达、店铺林立的邱集镇。他们鸡犬不惊,秋毫无犯,用现钱平价购买了少量米粮后,咬着自带的生姜,紧急向黑风谷方向撤退。午时,黑风谷口传出了密集的枪炮声,持续半日之久。南山姜,是这支队伍的御寒宝物,藏在衣袋里。《南山姜》入选届福建省龙岩市高三上学期期末语文试卷。《鄞江谣》练建安著江西高校出版社年10月 雄狮献瑞 “咚咚恰,咚咚恰,咚恰,咚恰,咚咚恰……”听闻这熟悉的锣鼓,增发按捺着内心的激动,不动声色,专心地经营他那摊“杭川牛肉兜汤”。 大年初五,是闽粤边的武邑岩前镇请客的日子。客家村寨春节期间请客的日期,都有定日。坐落在狮子岩的均庆寺,是定光古佛的祖庙。此日,格外热闹。 杭川,是闽西上杭县的雅称,此地与武平县山水相连,声气相通,同时于宋淳化五年建县,因此,百姓互称老友。“牛肉兜汤”是杭川风味名小吃。 增发的生意不错,一大早,卖了三五十碗。5文一碗的牛肉兜汤,每碗可赚一个铜板。照这个样子,10斤牛肉很快就可以卖完了,赚个百十文不成问题。 “初一落雨初二晴,初三落雨烂泥坪。”闽西正月多雨,昨夜下了一场连绵不断的“冷浆雨”,均庆寺前的石坪低凹处水汪汪的。阳光照射下,闪着金光,北风吹来,寒气逼人。 摊点冒着丝丝白雾状的热气,牛肉兜汤飘出阵阵香味。前来均庆寺游玩的客人,就有好些人被吸引了过来。 “牛肉兜汤”做法简易,以上等牛肉切成薄片,裹以薯粉,调以姜末、茴香、八角、酱油、鱼露等物,放入木鱼干、猪骨头熬制的滚汤中稍煮片刻舀出,晒上葱花、姜末。这样的天气,喝口浓稠爽滑的兜汤,正合适。 增发是上杭城肚里郭坊人,是“南狮”的师傅头。传说他打单狮可以轻轻松松地“缩”上两张层叠的八仙桌。前些年“杭川狮会”夺魁,得了金牌,名声很大。之所以来到里外的岩前古镇摆“牛肉兜汤”小食摊,说来也与“牛”有关。增发好赌,手气差,一次豪赌,急红眼了的他牵来大哥家的一头水牛,又赔了进去。他恨不得剁了双手,拈脚就走了,发誓要“以牛还牛”,赚回了牛本钱,再回杭川。 这一天,均庆寺也办狮会,号称“闽粤赣三省狮王争霸赛”。汀江木纲老板练大炮悬赏两银子的花红,奖励优胜者。这下可热闹了,周边客家地区来参赛的青狮足有18只,都是各县身怀绝技者。 百十丈外,是均庆寺。石坪上,人头攒动,锣鼓声声。这一边,增发指望快一点卖尽牛肉兜汤,收摊寄存在阿三哥的日杂店里,自家悄悄地挤入人群中瞧上几眼,解解馋。20余年的拳脚功夫,都被那些南狮锣鼓催醒了,发痒发麻。 一位老阿婆牵着小孙子过来了,叫了一碗。增发问阿婆要不要也尝一口,天冷,喝了驱寒。阿婆使劲咽着口水,说:“吃过了,过年喽,鸡汤都喝怕啦。”说着,抖抖索索地从上衣上摸出一块旧手帕,拣出5块铜板,反复数过,递到增发手上。小孙子喝完了,捧着空碗,舌尖舔着嘴唇,盯着老阿婆看。增发给他添上了半勺浓汤。小孩子乖巧地说:“阿叔新年发大财。”增发笑了。 就在增发抬起头的那一刻,他笑不起来了。他紧握铁勺的手有微细的颤动,双脚却坚实地扣在地面上。他看到了一群人摇摇晃晃向他的摊点走来。 为首一人,胡子拉碴,满脸疙瘩,敞开的外套,油污斑驳恰似剃刀布。他叫麦七,是古镇街头一霸,曾手持两把杀猪刀打跑了10多家赣粤外地客商,号称“大老虎”。还是去年腊月二十七,入年界了,麦七来到增发的摊点,连喝了5大碗牛肉兜汤。要付钱了,麦七从腰间摸出两把杀猪刀,插在摊点的木板上,说:“上杭老友,看看我这家伙值多少钱?拿去!”增发人在外乡,和气生财呢,还能咋的?陪着笑说:“虎爷,您开玩笑了。”麦七大笑,左手夺过增发手中的铁勺,只在木板的边沿用力一敲,两把杀猪刀跳将起来,右手抄接,两把杀猪刀又回到了他的腰间。 眼下,麦七又来了,还带着一帮人。增发能不紧张吗?老阿婆也怕“大老虎”,按下小孙子嘴边的瓷碗,牵着他慌慌张张地走开了。说话间,麦七就到了,用半根筷子残片剔牙,说:“上杭老友,新年发财啊。”增发笑了:“发财,大家发财。虎爷,您来一碗?”麦七说:“哎呀,新年发个利市,哥儿几个全包了。别忘了多搁些姜葱!”增发嗫嚅道:“5文一碗,算4……4文,中不?”麦七双眼一盯,缓缓道:“上杭老友,今日俺请客,咋啦,不给面子?” 增发将剩余的四五斤牛肉片全部倒入了铁锅里,不久,热气腾腾的牛肉兜汤就出锅了,调上配料,香气飘散。麦七和他那些朋友吃得满头大汗,连声叫好。一个矮胖客人说:“都说潮州湘子桥的鱼汤好吃,俺说这兜汤,真他妈的带劲。” 风卷残云一般,豪客们把这一摊杭川牛肉兜汤喝了个精光。锣鼓声声又紧密了起来,看来狮王大赛就要开场了。麦七竖尖了耳朵,他该结账了。增发说:“虎爷,28碗半,算您28碗,一碗5文,算4文,一共是文,您赏我文好了,整数。”麦七剔着牙说:“好,好。”他从腰间晃荡的杀猪刀旁摸出了一块银子,足有半斤重,晃了晃,扔进铁锅,说:“给,银子,立马找零,我等着用。”铁锅内有猪骨头和残汤。增发捞起银子,苦笑:“虎爷,我找不开啊,小本生意的。”麦七唰地拔出了杀猪刀,说:“要么砍下一块?一刀就够了。”增发说:“不,不要砍。”麦七收刀,张开巴掌伸出去,说:“你不要反悔啊。我等着用。”增发捧上了银子,说:“虎爷,您走好。”麦七推了增发一把,笑骂:“上杭老友,上杭拐哩!”前呼后拥骂骂咧咧地往均庆寺摇晃过去。 均庆寺外石坪,18只青狮跃跃欲试。场中,竖立着一根1丈8尺的桅杆,上头,以红绳悬挂一束雪里蕻。六张八仙桌依次按三、二、一的阵式叠好。哪一只青狮采下雪里蕻,哪一只青狮就是赢家,就是优胜者。1丈8尺的桅杆实在是太高了,往常,“缩”上两张八仙桌高度表演的青狮,就算是方圆百里的高手了。3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要么怎么叫狮王争霸赛呢?主办方为安全计,在桅杆的四周铺设了一层层谷笪,谷笪下铺垫有厚厚的稻草。 主事宣读完规则,鞭炮炸响,接着就是一下重锣。赣南远客为先,6只青狮在锣鼓声中一跃奔出,翻滚跌扑,煞是好看。不料,来到谷笪处,纷纷栽倒,折腾了半炷香工夫,就是挨不近八仙桌,只得退场。粤东也是6只青狮,无意上八仙桌采高青,成双结对表演了一套“雄狮献瑞”连贯动作,吐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红布条幅。锣鼓停歇,恰好回到了原处。现在轮到闽西的了,也是6只。先出4只,舞到谷笪上,也接二连三地栽倒了,退了回来。剩下的两只,一只是当地的,一只就是杭川郭坊的。郭坊的锣鼓敲起,有些乱。增发拨开人群,来到狮头旁,抚摸着狮子耳朵。狮头移开,露出了他大哥的脸。大汗淋漓的大哥又惊又喜,说:“好你个发狗,躲在这里修仙哪!”增发说:“大哥,我来,赢钱还你水牛。” 说话间,锣鼓声响了,岩村青狮已经奔跳出去老远。郭坊青狮欢快蹦达,一会儿工夫,就追了上来。岩村青狮上谷笪了,摔倒、爬起、摔倒、爬起,一副不屈不挠的架势。郭坊青狮在谷笪外停了停,嗅了嗅。鼓点骤响,郭坊青狮一跃而起,落地生根。每走一步,大吼,四脚齐齐发力,顿一顿,似有千钧之势。围观者听得谷笪下面发出脆响,仔细听听,是谷笪下滚动的圆竹杠破裂的声音,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围观者大声喝彩,一浪高过一浪。岩村青狮伏地不动了,狮头大口大口地喘气,冷汗湿透了后背,手脚发抖。他想,看不出这卖牛肉兜汤的,功夫竟是那样的高深莫测。怎么办呢? 岩村狮头不是别人,就是那只“大老虎”,麦七。 《雄狮献瑞》入选福建省龙岩市年高中毕业班第一次教学质量检测语文试卷。 长篇小说《南行记》练建安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年8月 九月半 大雨,倾盆大雨,闽粤赣边客家话所言竹篙雨,丰乐亭瓦片“嘭嘭”作响,一会儿工夫,茶亭的屋檐就挂起了一道断断续续的珠帘。丰乐亭外,有一把棠棣树枝探入了窗内,一嘟噜一嘟噜的金黄棠棣,滚动水珠。“棠棣子,酸吗?”说话的是一位壮年汉子,敞开黑毛浓密的胸膛,手持酒葫芦,蹲踞在一条板凳上,剥吃花生。他身后的墙壁上,靠着一大梆刀枪剑戟家伙什。看来,他是做把戏行走江湖的。“没落霜,样般有甜?”说话的是花白胡子老人,干瘦干瘦的,老人闲不住,时常挑一些花生糖果来茶亭售卖,他的张记糠酥花生是很有名的。“老伯,您这糠酥花生地道,再来半斤!”汉子将最后一把花生壳碾碎,摊开手心,恰好吹来了一阵山风,粉末就纷纷扬扬飘出了茶亭之外。丰乐亭外石砌路上,一行人匆匆忙忙地闯了进来,他们是打狮班的,为千家村的张禄贵老太爷八秩诞辰祝寿,赢得了满堂彩。几封银子的赏钱,使他们难以抑制兴奋,他们不顾乌云密布,执意要当日返回枫岭寨。半途,大雨就来了。闽西山地多草寮,他们齐齐窝在一个路边山寮躲雨,伏着雨空子,猛跑一阵,就来到了这丰乐亭。“花生,糠酥花生哦。”花白胡子拖腔拖调地叫卖。这群汉子咽着口水,捂紧口袋,竟然没有一个人过来“交关”。花白胡子又吆喝了一声,就有一个汉子说话了:“老人家,您老就别吆喝了,俺们不是猴吃牯。”花白胡子自讨没趣,悻悻然,道:“没有钱,就莫充好汉。”汉子说:“好,好,俺们没有钱,不是好汉,可也不是猴吃牯哟。”说着,有意无意地摆弄着钱袋子,哗哗响。大家都呵呵笑了。花白胡子的脸,当场就黑了下来,把头扭到了一边。那个做把戏的,也有些不高兴了,什么猴吃牯猴吃牯的,难听。客家人把那些个贪吃而又不顾体面的人,叫作猴吃牯。做把戏的站了起来,虎背熊腰,天暗了大半。他好像有些醉意了,大声说:“什么猴吃猴吃的,不买,就行开去,莫耽误人家做生意。”“噫?俺们又没有撩拨你,你出什么头?这又风又雨的,荒山野岭,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做什么生意?”汉子也不高兴了。“俺也没有撩拨你们哪,你们人多,俺也打不过,乡里乡亲,没得打。就讲啊,俺老马刀可以把话撂在这里,单挑,你们的狮头增发,也搬不动俺这小半条腿。”做把戏的原来是闻名江广福三省的老马刀,他放出了狠话。汉子说:“俺就是增发。”老马刀说:“试试看?”“俺不是牛,干吗要相斗?”“搬得动吗?”“搬不动。”“没有试,怎么晓得?”增发说:“还要试吗?你脚下的麻石都开裂了。”老马刀说:“得罪了!”增发说:“还说不准是谁得罪了谁。十年后,俺来找你。”老马刀说:“九月半,俺不走,三河坝等你来。”花白胡子下山,就把丰乐亭的故事讲开了,免不得添油加醋。他说,增发上前抱住了老马刀的大腿,老马刀一发力,增发就飞了出去,还摔断了两颗门牙。巧的是,那日山路湿滑,增发摔了一跤,刚好跌坏了两颗门牙。增发百口莫辩啊。这十年,增发时常忍受着人前人后的指指点点,辛苦做工,厚脸过活。有人说,他拜了癞痢僧人为师,苦练一种常人忍受不了的功夫。可是,谁也没有见他露过一手半手的。增发变了,正月大头的狮子庙会也不凑热闹了。他沉默寡言,看上去有些呆。这一天,是第十年的九月十三日,增发从上杭县城搭船下行百八十里,抵达河头城。增发在街上行走,过木纲行,门前大石狮突然倾倒,增发飞起一脚,将大石狮踢回原处,位置分毫不差。其快如闪电,门子疑在梦中。还是有人看出了名堂,增发功夫了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三河坝。有人就劝老马刀外出躲一躲,老马刀断然谢绝。徒弟们群情激昂,要拼了。老马刀摆摆手,叫他们都退下,没事,自有办法。九月半,是决斗的日子。九月半,诸事不宜。这日早上,老马刀独自一人在汇城东南角的一个老旧庭院里,生火熬稀饭。稻米在砂锅里翻腾着,清香四溢。老马刀忍不住一阵咳嗽,浓痰中夹杂血块。前年赣州圩场比武,伤了人,自家也落下了内症。他突然感到很孤独,很悲伤,很失落。他有些艰难地站了起来。这时,他看到了一个人,他等了十年的人。增发右手握刀,左手提大包裹。老马刀说:“晓得你一定会来的。”增发说:“俺一天也没有忘记你。”老马刀说:“是你的,就该还给你。”增发放下大包裹:“这是你的。”老马刀疑惑不解:“什么?”增发说:“利息。”老马刀低头打开包裹,是梁野山金线莲。他想说些什么,却说不出来,呆呆地望着增发的背影慢慢消失在汇城墙角拐弯的地方。《微型小说选刊》年24期散文集《回望梁山》练建安著海风出版社年12月 与唐老弟谈长篇及微篇小说创作 唐老弟:您好! 我在福州过年,很想念家乡亲朋。春节期间,我特别集中看了些微型小说。关于微型小说,您老弟是我的前辈。十多年前,您的《朋友》入选《中国微型小说年选》,漓江版的。那时,选本不多,漓江版年选是最权威的年选。这创造了闽西第一,轰动了杭城文坛。您后来写了篇《师兄金鑫》,以在下单位故事为原型,在《闽西日报》发表后,我的老领导对我很有意见,说:“好啊,你个小练,你是英雄救美。我呢,是每天对着一个干事念文件读报纸的老古董。”麻烦不小啊。那时的唐老弟,写微型小说,是个大牛哥。后来,我们一起写大人物传记。再后来,您调到龙岩城,写剧本,写散文,写论文,写长篇小说,十八般兵器都用上了,四处开花,硕果累累。尤其是《海峡情缘》长篇小说三部曲,一出手就是接近万字,中国作协还列入了重点扶持。我想起了十一年前,《福建文学》原常务副主编、福州大学教授施晓宇先生的几句话:“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这个唐老弟,迟早要震惊当地文坛。”现在看来,这个“当地文坛”,可以指福建省,也可以指闽西。我认为,唐老弟目前长篇小说领先闽西当地文坛的评介,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不过,老弟啊,我还是以为,微型小说好。您在写长篇的同时,写写微型小说吧。为什么呢?请允许我说说理由:其一,当今很少人有较为充裕的时间看长篇小说,如果有,他们首选看经典,看名家作品。中华大地,人才济济,我等写长篇,有多少人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ongtongzia.com/xtztp/7309.html
- 上一篇文章: 年天猫花园生活节,美轮美奂,l
- 下一篇文章: 这样说话的人,一定不要深交深度